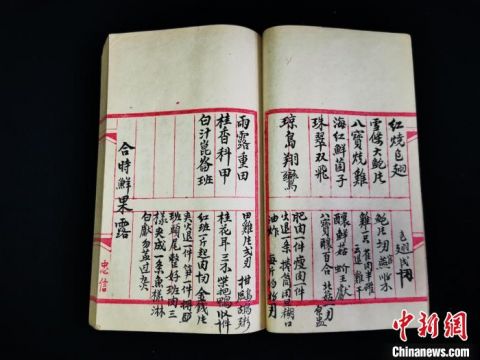幸运的倒霉蛋儿——一名中央集团军群青年军官的战争往事(下) 每日头条
更多硬核,有趣,好玩的文章和资讯,请点击上方芬里尔战史研究关注获取!
......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天一亮,我就动身前往团指挥所获取进一步的命令。我带上了死去的上尉。我们让他半躺在挎斗里。我爬到座位后面,把他的头放在我的膝上,然后合上他的双眼。他那张平时活泼而熟悉的脸带着巨大的陌生感和难以言说的疲惫。那是一段上坡路,我们沿着乌拉小河山谷的林区小路,来到团指挥所所在的木屋。我团的指挥权,或者说我团残部的指挥权,已由阿努尔夫·冯·加恩少校接管,他此前是师属燧发枪营营长。在我做报告时,团部的两名传令兵在花园里挖了一个坟墓。米勒的尸体被放在里面。冯·加恩少校和一些人站在坟墓周围,他开始念“我们在天上的父”,在场的所有人都随之念了起来。然后我们把土撒在包裹尸体的防水布上,沉默的人们把坟墓填平了。
阿努尔夫·冯·加恩少校,他于1944年9月2日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
我们的营没了营长,之后是由马尔维茨(Mallwitz)中尉接任指挥。他在1943年8月6日至9日期间担任过6连连长,当时他的大腿受了重伤,但他守住了伊万诺夫(Ivanowo)村。我和他一起乘坐挎斗摩托车前往我们的指挥所。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再次进攻拉贝基。有了前一晚的经验,这次我们要更狡猾一点才行,不能再有任何以连为单位来实施进攻的想法。我们的计划是,半个营一起前进,绕过右边的松树林;另一半兵力则与马尔维茨和我一起,要在位于陡峭河堤上的战壕里前进。我记得我还看了看自己之前摔落的地方。敌人在夜间建立起强大的防线后,我们对新一轮的进攻没抱丝毫成功的希望。
当我们第二次进入拉贝基村时,那里一片死寂。尽管敌人肯定早就看到了我们的行动,却并没有开火。终于,在踏上最后一段路程时,我们按照命令喊着“Hurrah”,冲入了阵地。直到最后一刻,我们还在担心敌人之所以会让我们靠近,只是为了更有把握地用上所有的武器来消灭我们。但结果他们没有进行抵抗。红军士兵们举着手,从战壕和地堡里爬出来投降了。我们俘虏了四十人;缴获三门反坦克炮、一辆德国突击炮,还有迫击炮和机枪。此外,有六名受伤的德国战友被释放了。他们隶属早先占据这个支撑点的部队。他们受了重伤,就没有被送来,但俄国医护兵已经为他们包扎过了伤口。
我们对拉贝基这场小小胜仗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。据报告,更右翼的一处被突破了,因此必须将战线后撤。到了下午,当我们几乎还没有机会在拉贝基站稳脚跟时,形势似乎已经变得危急起来,与右翼的联系也再次中断。在我们后方沿乌拉河山谷的莱佩尔-乌拉(Lepel-Ulla)公路上,有大批的车辆开过。很明显,所有可以行驶的车辆都在向乌拉小村开去。因为谁都想从那里过桥,这样就能抵达更远的公路进行撤退了。
与此同时,我们急切地等待着撤退的命令。当它最终通过无线电下达时,显然已经太迟了。分散在各处的2营部队撤回乌拉河山谷时,路上已经出现了失控的溃逃场面。我看到飞奔的辎重马车、各种机动车辆,其中还有徒步赶路的士兵们。那些车上都装满了人员和物资。显然,俄国坦克就要从他们的后面追上来了。我们的耳边传来轰隆隆的声响,逃亡的人们被驱赶到前面。那是一幅溃逃的景象,逼近的敌人坦克用他们的火炮和机枪火力,扫荡着处于恐慌中的我营残部。
现在任何一名指挥官都不可能再拦住他的部队了。马尔维茨中尉突然不知所踪,我就命令还在身边的少数营部成员,从某处渡过乌拉河,并在对岸会合。因为要去到乌拉桥渡河显然是不可能的了。在路边的壕沟里,我突然发现又只剩自己一个人了。有两辆敌人的T-34坦克从我边上全速驶过,它们上面都挂满了步兵。这种奇异的情况让我错愕不已,我甚至都没有想过要在后面朝他们开火。我没有掩护,就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。而接下来的理性思维促使我跃过公路,去到河岸边。
紧追不舍的T-34/85
我再次完全冷静下来。为了方便渡河,我准备去找块木头来,结果我找到了一根货真价实的横梁。随后,一名医护兵加入了我。他长着一头红发,是我营部的博伊勒克(Beuleke)。去年秋天,我在阿索罗瓦(Asorowa)公墓认识了他。博伊勒克已经脱得只剩内衣裤了,他说他不太会游泳。我把那根相当于铁路枕木尺寸的横梁搬到水里,然后让博伊勒克在我前面坐上去,这样它就可以把我们两个都安全地带走了。博伊勒克死死地抓着木头,我就让他把手臂向两边伸开,沿着水面平放,这之后情况才好了一些。我穿着整套制服坐在博伊勒克身后的横梁上。在我们的体重下,它下沉了大约半米,因此我们的胸部被水淹没了一半。
这条小河近20米宽,应该可以轻易而快速地渡过。不过,我仓促构思的计划是要利用水流顺流而下。我打算连接一支同去对岸的规模更大的队伍。在右岸,各级士兵都在丢弃他们的武器、装备和衣服。我尽可能大声地呼喊,让他们去为自己找块木头。但许多人已经陷入了恐慌,会游泳的和不会游泳的都在往河里跳。
沙伊德鲍尔与战友们泅渡的是乌拉河的一条支流,水深0.6~3米
与此同时,我用手操纵着横梁,并小心地不让我的机枪被打湿。在坐上梁横前,我用一条很短的带子把机枪系在了脖子上,这样就算我们半个身子都被淹没,它也不会浸到水。当我们在几近奔腾的河流中绕过弯道时,阵阵机枪火力扫射到河面上。我挣扎着环顾四周,想看看射击只是碰巧打中了河面,还是我们被敌人发现了。在移动过程中,我右脚的胶靴无意中掉了。它已经被水灌满,水流直接就把它给冲走了。我气得干脆让左靴也随它而去,左靴也是轻易地就滑落了。
在经过令人难忘的一公里的水上之旅后,我发现冯·加恩少校正站在左岸穿靴子。他独自渡过了河,他是个细心的人,在渡河前已经把靴子脱掉了。我向他划去,然后我们爬上了岸。
第252步兵师战史(第205页)对这一系列事件作了如下记录:
“6月26日,敌人在多处渡过乌拉河,并从后方还有大部分从两侧包围了那里兵力薄弱的阵地。疲于战斗的士兵们——自6月22日以来,他们一直在不眠不休地战斗,吃的食物也很少——在弹药耗尽后,试着边打边退,撤过汹涌的乌拉河。少数幸存者冒着敌人的炮火,在没有桥也没有船的情况下,设法抵达对岸。不会游泳的人像葡萄一样挂在会游泳的人身上,把他们拖进河水深处;会游泳的人一次次地尝试拉着伤员过河,直到体力耗尽。在那里,潮湿的死亡获得了丰富而残忍的收成。第二天早上,路上出现了个别赤身裸体的人,他们除了一把武器外什么都没带。大家想尽一切办法为这些人找来新衣服,只要他们能够重新加入战斗。”
博伊勒克和我与冯·加恩少校一起从乌拉出发,走上了一条通往南方的公路,这也是一条前所未有的撤退之路。去年和我一起在阿索罗瓦逃脱的博伊勒克离开了我们,因为他想去找辎重队,重新弄一套制服,而且不是只有他一人如此。各级士兵都沿着这条公路过来了,他们仍是行色匆匆,许多人没有穿制服或只穿着内衣,他们也没有武器和装备。我几乎穿戴整齐,只有两只脚光着,我朝他们跑了过去。冯·加恩说,团部的联络官克鲁格(Kruger)中尉在团指挥所拉了一条跨河的缆绳,这样十五个不会游泳的人就可以拉着它过河了。我们营的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米勒军士长也不会游泳。他说他穿着背心过河,骑士铁十字勋章就包在军帽里戴在头上。为了保护桥上拥挤的交通状况,一门反坦克炮被部署在那里。头脑清醒的炮组成员们正在一辆接一辆地向冲入的坦克开火。
我仍然光着脚,协助少校把凡是隶属我们部队的归来人员都集合起来。但人群中有一名来自装甲歼击部队的少尉,他和我一样也没穿靴子。正午的烈日很快就把我们的衣服晒干了。我没了靴子,而我不用为丢失靴子负责,这个事实却没有带给我多少安慰。但我保住了武器、弹药、地图包和制服。虽然我很高兴少校没有把损失归咎于我,但我也为自己所呈现的不体面的光脚军官形象而备受煎熬!我们很快就把第7团的残部集合起来,并把我营的剩余兵力补充进了该团。
团部的小型辎重队只有所谓的“轻型防毒服”,听说其他制服和鞋类储备都在我们身后80公里处的辎重队那里。在团部的“连队之母”可以弄到一双像样的靴子之前——也许是从一名伤员那里去弄——我只能先穿着那双著名的“好鞋”对付一下。它们包括坚硬的鞋底和从鞋底延伸到膝盖的石棉套,通常来说是绑在膝盖下方的靴子上。但这款鞋从来没有在二战中正式投入使用过。我就穿着这样一双临时安排的不让你正常行走的鞋子,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,也就是在第7掷弹兵团团部担任第2联络官。在接下去的几天里,我和来自柏林-夏洛滕堡(Berlin-Charlottenburg)的第1联络官克鲁格中尉一起,执行了极其危险的任务,我们驾驶机动车沿着危机重重的路线行进。
(全文完,感谢阅读)
原创不易,请三连支持我们!